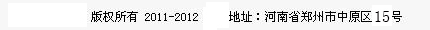秦渡人与戏秦渡镇,人称“戏窝子”。秦渡镇有三座戏楼,城隍庙前、关帝庙(当地称老爷庙)、药王楼各一座。城隍庙戏楼 ,五间宽,场地也大。临时当做戏院也不少,如“裕和家园子”、“张家园子”、“梅李园”,随时演戏,随时搭台。庙会报赛、逢年过节都唱大戏。这里是万商云集之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河南商人和商贩,还有民国时逃难来陕谋生的落户难民,这里是一个陕、豫、晋文化交汇之地。在这里演唱过“汉调二*”,也演过“河南梆子”或豫剧。豫剧出名的有常香玉作主演的“狮吼剧团”等,曾轰动一时。户县是“眉户”的发源地之一。户县和眉县一带自古盛行一种民间歌曲,古称“清曲调”,户县人称之为“曲子”。眉户开始在关中地区流传,华阴、华县一带是周朝郑国地域,受“郑声”的影响,不断发展。所以,眉户有东西之分,这里应该是西路眉户。清朝乾隆年间,随着秦腔等各地戏曲艺术的发展,眉户逐渐被搬上舞台,形成一种颇受欢迎的剧种,在演唱形式上仍然保留着地摊演唱的形式。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板胡和海笛相辅,连拉带唱,既是演奏员,也是演唱者。民国期间,秦渡当地经常演唱眉户的民间艺人有数十人之多,活跃于街头巷尾。它不同于秦腔的高昂激扬,豪放粗犷,眉户的唱腔较为细腻委婉,优美动听,富于表现深沉、凄楚和悲痛。其唱本多为折子戏,如《张连卖布》、《脏婆娘》、《安安送米》、《杜十娘》等,新编剧目有《兄妹开荒》、《大家喜欢》、《十二把镰刀》等。现代剧《梁秋燕》是眉户剧的代表曲目,当时有“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的一说。汉调二*也是流传于陕西的一个剧种,即陕南花鼓戏。流行区域以秦地为主,关中一路以西安、三原、泾阳为中心,流行于富平、咸阳、凤翔、户县、临潼、蓝田一带。范紫东等人称之为“秦声吹腔,古调新声”,与现称梆子秦腔同源异流。据《户县志》记载“汉调二*,清乾隆年间传入户县,在县城有两个戏班,秦渡镇、大王镇也曾有松散的戏班。”汉调二*唱腔有西皮、二*,与京剧是姊妹关系。年曾有王安奎领班的“明盛社”在秦镇北街当铺演出,其班子强把式多,演出很成功。当时有冯志才(须生)、张庆宏(文武旦)、张鸣岐(须生)、刘某某(坤角,花脸)等。后来有原老板领的二*戏及其他社团也来过,这些对秦渡镇群众影响较大,于是便出现了许多二*迷。年前后,有潘大、姜生彦、四喜子、郭老四等,在秦腔自乐班的基础上组织二*自乐班社。经过一段时间排练,能唱不少折子戏。年在镇西街戏楼登台表演,演出《临潼山》、《捉放曹》、《摸包》等剧目,受到群众的热捧。后又有县城二*把式山鸣岐、赵明瑞、山崇宏、韩宗旺等名家加盟,在秦镇与其它剧种唱对台戏,群众普遍认为二*戏唱得 。秦腔在秦渡最盛行。清同治末年,秦渡镇秦腔世家李银福组建金盛班,经常应报赛与庙会演出,光绪年间在关中颇具盛名。班内有恩科子、李银富、万成子等名演员。晋公子、*金亮、茂盛儿也曾搭该班演出多年,光绪末年金盛班解散。恩科子(艺名兰州红),饰演《金台将》中的田单,《机房训》中的薛保,壮烈悲愤,声情并茂。李福银(金盛班班主)工须生,声如铜钟,纱帽、道袍戏俱佳。拿手戏有《金沙滩》、《湘江会》、《祭灯》、《调寇》等,开口即音润韵足,字正腔圆,人称“秦中数十年来须生之冠”(王绍猷《秦腔纪闻》)。万城子,为李福银高足,《双灵碑》等杨家戏,刚毅豪爽,气派宏大,十分动人。金盛班还有李年儿(人称假福银)、刘五儿(净角)等皆文武全才(《户县志》)。《户县志》第三章.戏曲:“李云龙(黑娃),秦渡镇人,工媒旦,乡间有‘黑娃摇手’之说。”李云亭(-)艺名麻子红,秦渡镇沙道巷人。少年于私塾读五经四书,15岁在西安中和班学艺,后加入德胜班、玉庆班为台柱,文武须生样样精通,嗓音宏亮,扮相俊伟。每场演出都能博得通场喝彩。年易俗社成立,被聘为教练。年加入榛苓社,两年后进三意社,作短期演出后回家。李云亭演出扎靠戏有《火牛阵》中的田单,《拆书》中的伍员,《下河东》中的赵匡胤,《金沙滩》中的杨继业。纱帽戏有《十五贯》中的况钟,《八件衣》中的杨廉,《闯宫》中的梅伯等。其演《拆书》中的伍员,一出场威武雄壮,器宇轩昂,马鞭一抖,走至台口,观众说其“真像一只老虎”。念完家书后,怒发冲冠,首句“大堂口把豪杰气炸肝胆”中的“大堂口”三字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立即激起通场叫好;《太和城》鞭打殷夫人和五雷击柱,动作准确妙绝;《闯宫》中梅伯抱炮烙能挂起三样口条(胡须)。其与衰派老生刘毓中之父刘立杰(木匠红)是当时秦腔界并驾齐驱的人物。和 旦角陈雨农(小名德娃)合唱《走雪》,民国年间被灌成唱片发行。李云亭不但精通秦腔,也精通曲子(眉户),能弹三弦,亦能唱汉调二*。年病逝,年仅51岁,戏剧界及观众深感遗憾,西安的回族同胞说:“想吃桶壮的人参有,想听麻子红的‘大堂口’没有了。”户县文人王觉生说:“除过麻子红的戏,谁唱我都不看。”由于浓郁的戏曲文化影响,秦渡镇及其附近出了好多 戏曲演员。从镇内走出去的秦腔演员,除李云亭之外,有韩志珍(小名长安)。近代 的有乔新贤(见名人录)、郭辅中(秦镇北街人,原汉中新汉社 须生演员,团长、导演)、薛志秀(见名人录)、杨桂琴(秦镇南街人,咸阳大众剧团 旦角演员,有“金嗓子”之称)、鲜新民(秦镇北街人,岐山剧团 演员,有“活周瑜”之称)等。像 丑角演员阎振俗(细柳姜仁村人)、田德年(长安东甘河人)、杨金声(南留村人)都出生于秦渡镇附近。秦渡镇懂戏的人多,看戏也很挑剔。这些戏迷中的一些人,“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筐”,对戏词却背的滚瓜烂熟,一字不漏。凡是在秦渡演出的,不管是普通演员,还是名家名流,无不小心谨慎,稍有闪失,就会引起躁动,嘘声倒号,弄得你下不了台。据说,秦腔名家苏育民某次在秦渡出演拿手的折子戏《打柴劝弟》时,舞台动作不到位,遭到“轰台”,落了个“脸红”。户县宣化剧团的当家演员曹韵卿,唱腔优美,戏功扎实。据说,一次在《花亭会》的演出中,有一节扳辘轳的戏段,细心的观众仔细数着台上演员扳放辘轳的回数,看是否相符。对演出的要求近于苛刻,可见在秦渡唱戏之难。演戏的时间主要在过年、农历四月八、八月六两节。除了西安的“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五一剧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等大剧团外,演出最多的当数户县宣化剧团(后改名为户县人民剧团),每次演出十多天。“八月六会”演出,正逢雨季,有时一住二十多天,所以当地群众称之为“雨背篓”。由于观众太多,西街戏楼容纳不下,一般在空地或学校操场临时搭台演出,拥挤踩踏时有发生。户县剧团当家演员曹韵卿,“嗓音清亮,音程远达,久唱不哑。其狠戏,吐字清晰,尤以苦情戏为佳。时在西安北关、南大街等剧场主演《安安送米》,连演半月座无虚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主演《安安送米》的名家杨金凤,偕秦腔名流刘易平、田德年等看后无不叫绝。曹韵卿在户县观众心中非同一般,以至于当时,将‘户县人民剧团’叫‘曹韵卿家戏’。”演出一般都是卖票演出,而且票价不菲,每天几毛钱的戏票钱,对当时省吃俭用的农民来说,是一笔不算太小的开支,为了看曹韵卿的戏,都说值得,所以就有“为看曹韵卿,哪怕做贼挖窟窿”的说法。五十年代初,没有电声设备,没有扩大机,全凭演员的好嗓子。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剧场内外到处回响着演员的戏声和观众的叫好声,夜深人静,戏声远传数里之外。电光布景也是以后才有的,记得一年西安某剧团在北堡子的演出,头一次的“电光布景”,引起轰动,记得好像是秦腔《追鱼记》,有好多不常看戏的也前来看稀奇,戏园子里人山人海。这里的人们懂戏,爱戏,所以关中地区各剧团也喜欢到秦渡演出,除了西安的各大剧团外,咸阳大众剧团、人民剧团,陇县剧团、岐山剧团、眉县剧团、周至剧团都到秦渡演过戏。焦晓春、郭明霞、肖若兰、王玉琴、苏育民、任哲中、李爱琴等常来演出,为人们所熟知,深受喜爱。像田德年、杨金声、阎振俗因为是本地人(离此地不远),更不用说了。十年文革,老戏被当作“封、资、修”,遭到禁演。剧团解散,保留下来的只有西安的几个大剧团。除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以外,其他都处于停演状态。秦腔名流受到迫害或下放劳动。如田德年、闫振俗等都被遣送回乡。 的秦腔名家袁克勤,被下放到宝鸡虢镇,因不堪受辱而 身亡。户县人民剧团的曹韵卿,被戴上“反动戏阀”的帽子,受到批判和冲击,被迫离开舞台,安排到县文化馆看大门,身患半身不遂,仍拄着拐杖艰难值班。70年代初,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在秦渡演出《红灯记》,吴德饰演的李玉和。久违的和声扑面而来,高昂激扬的唱腔,激荡着戏迷的心扉。在他们积极奔走,相互联络,紧锣密鼓的张罗下,西街的“秦五剧团”组织起来了,北街的戏迷们也坐不住了,一群人围绕在从“新汉社”返乡的秦腔老艺人郭辅中身边,物色角色,组织乐队,置办戏装,《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很快地搬上了舞台。后来,在省群众艺术馆工作的左明中,带回蒲剧剧本《槐树庄》,并同郭辅中先生一起改编为秦腔。排练上演,立刻引起了轰动,不断地受到外地邀请。在周围几十里范围内的演出,场场爆满。一次,在长安东祝村演出,赋闲在家的秦腔名家田德年听乡邻称赞,看了后赞不绝口,夸道:“一个农村业余剧团能把戏演到这个份上真不简单。”后来受邀到西安西郊演出,连续演出十几场,场场满座,轰动一时。参加演出的演员都是从来没有上过舞台的泥腿子,平时的耳濡目染,艺术熏陶,秦腔的灵*已经渗透到骨子里了,再经专家点拨,一招一式,富含戏情,活脱脱的戏剧人物形象,展现于观众面前,为人称快。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一股“秦腔热”,“自乐班”遍地开花。除了家庭堂会、婚宴助兴,而且参加各大电视台的“秦腔大赛”,获得得奖演员的称号。闲暇无事,戏曲爱好者三三两两,相聚一起,一板一眼,入弦入味,自拉自唱,自娱自乐。生活的艰辛,家事的烦恼,一切都抛之九霄云外,欣欣然,陶陶然。秦渡*酒秦渡镇这座古老的城镇,从金元开始直到解放,这里一直是关中地区 的稻米集散地。这里和*酒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的真正意义的“宪法”——《周礼》就产生于此,《周礼》中就有*酒制作和管理的明文规定。中国古代 部禁酒令——《酒诰》也产生于此。根据古文献《周礼》记载,西周在这里建立了管理和酿酒的“酒正”,除其编制人外,还有专门酿酒的酒人、酒女人。平王东迁后,这些酒人、酒女大多流落于此地,几千年来,传统的制酒工艺代代相传,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成为非物质遗产的“活化石”。人常说:“水是酒之血,米是酒之肉,曲是酒之骨,味是酒之*。”一个好酒离不了好的原料。秦镇东边紧靠的沣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水质的清冽在古代是很有名的。老子说:“丰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尘垢,金铁在中,形见于外。”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沣河上游水源分析,其pH值为7.17,硬度为.7mg/L,比对世卫组织对水质划分的标准,属于弱碱性,硬度较大的水源,水中富含矿物质。这一特点有利于酿造过程防止酸变和糖化酶及酒精酶的合成。明清以来,这里原来盛产大米,尤其是高品质的圆糯,其直链淀粉含量高,是*酒酿造 的原料。沣河滩的野生辣蓼(制曲的重要原料),为酒曲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资源。这里还盛产*酒曲的主要原料——乌头,当地人称为乌药。在秦渡镇街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家中药店,有名的有通顺堂、半济堂、咏仁堂等,这些中药店以收购和加工乌药作为主要业务,同时也制酒曲销售。秦镇的水米曲诸条件具备,体现“酒之*”的口味也必然独特。这里的*酒和外地 的区别是含糖量较小,口感略带苦味,本地人称之为“苦头酒”,由于酒劲猛,曾被秦腔表演艺术家闫振俗先生诙谐的称之为“跟头酒”。其原因除了因为发酵彻底,大量的糖分转变为酒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酒曲中的中药成分,三十几味中药各有用途。这里的广药非常有名,各个酒作坊所用广药各不相同,每个药店也都有自己独有的广药配方。所以,酿出的*酒风味又各具特色。秦三医疗站的周青坤,是秦渡镇半济堂中药店的后人,祖上是湖北人,来此经营中药材生意,落户秦渡镇已有二百多年。家藏有制*酒的广药配方,其介绍的几十种广药的功效,基本与王宗西先生所说相似:“良姜、草蔻、桂皮、八角、甘松、山奈等辛热药以养胃醒脾;陈皮、青皮、半夏以理气化痰;茯苓、猪苓、防已以渗湿利水;羌活、细辛、白芷、杏仁以解表散寒;五味、 (微量)以收敛散痞。”特别提到*酒曲中用量 的乌药加工,要用急火爆炒,其火候最为关键。乌药内含有*的“乌头碱”,只有在高温下才能降解。火候过大,乌药失去原有的药性,直接影响到*酒的风味;火候过小,就会引起中*,所以一定要掌握好。加工处理的乌药在中药叫附子,是一种大热大补的药材。其作为酒曲主料,不但影响*酒的品质,而且增强*酒的医疗功效。抗日战争期间,东南大部国土沦陷,西安屡遭日机轰炸,大量沦陷区人来秦镇谋生,使得秦渡镇一度商贸非常繁荣。有大小商户二百余户,有大小*酒馆十余家,规模较大的有醉仙楼、同乐园、康乐居、大盛馆等,加之农村普遍家酿,使这里的*酒业得到长足发展。遗憾的是从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镇里的*酒馆相继关门停业。现在街上的长安居、咏仁堂两家酒馆,也是80年代后重新开张的。从秦三村薛姓家谱看,这支叫“元门馆”的薛姓大户,其祖先于清同治以前在秦镇开一酒馆,“元门馆”是酒馆的字号。百余年来,人们一直以字号称呼这一族人。可从侧面看出酿酒业在秦渡镇历史上的概况。解放后,尤其是统购统销后,由于缺乏原料,*酒业逐渐萎缩。改革开放后陆续有几家*酒馆开业,一是国内知名*酒的冲击,其次本地*酒业酒曲的原料成本的高涨和伪劣*酒的低价倾销,综合影响本地*酒业的发展。*酒业何去何从,前景令人忧伤。秦渡镇南街有长安人滑有济开的“长安居”*酒馆。滑先生的父亲滑天泰,清末至民国时,曾在秦镇街道开酒馆几十年。根据家中现存的“馀德堂”印鉴和镌有“万历四十年”字样的铸铁蒸甑推算,其家开始经营酒馆距今有四百多年历史。铁蒸甑是蒸料用具,为酿酒的主要器具。印鉴是当时的字号为了用于购买大米药材等原料签订合同,也是酒馆的商标和名片。据滑先生谈,“馀德馆”是他家原来的 名,这从遗留下来的锡制酒器上刻有的“馀德馆”可以说明。民国年代的“醉仙馆”曾出现在王宗西先生所撰写的《户县*酒》一文中:“清末到解放初期,户县县城和秦渡、大王、庞光三镇共有酒馆二十几家,酒馆的名称也很雅致,如户县的聚仙亭、陶然居、永乐馆、忠义园。秦渡镇的醉仙馆、同乐园、康乐居、大盛馆等。”据滑先生讲,今天的长安居就是王先生所讲的“醉仙馆”,最早叫“余德馆”,后来又改成“醉仙馆”。滑先生兄弟数人,子承父业,都开有自己的*酒馆。90年代初,滑先生率先在西安旅游景点——大雁塔附近开酒馆,取唐代 诗人白居易的典故:“长安居,大不易”的前三个字作为酒馆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二.白居易》载,白居易年少未出名时,以文进谒顾况,顾况见他年轻,有点瞧不起,于是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顾况运用双关的手法,以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但看到白居易的那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诗后,不由得赞叹起来:“这诗写得真好,你住在长安是容易的了。”)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马文瑞为之题写了馆名。“长安居”在西安小有名气。但时间不长,周围村子跳出七八家*酒作坊,良莠不分,劣质*酒充斥市场,价格直线下降。滑先生为保证*酒质量,严格用料标准,按照老传统工艺,生产成本较高,加之原料涨价,尤其是做曲的乌药货源短缺,价格高得离谱,致使*酒生产的成本直线上升,缺乏价格优势,加之宣传力度不够,生意不尽人意。咏仁堂*酒馆,位于南街楼下坡的丁字街口,为蒲建国先生经营。蒲先生咏仁堂的建筑,远溯清末民国户县酒馆的典型风格,主人住在前房,酒馆在远离街房的后边,中间长长一间过道,通往后边的厅房,一边是烹饪和热酒的厨房,往前走,进入客厅。客厅上下两层(不算地下室),一层客厅有账房,有宴客间。整个酒馆典雅大气,古色古香。顺着装修华丽的楼梯进入二层,是一个宽敞的大厅,成排的桌椅,幽雅静谧的环境,确是游客休闲饮酒的好去处。高大宽敞的地下室,里面摆满发酵的大缸,以及成包成包的中药材,这里是*酒的生产车间。由于处于底层,温度恒定,确是酿造的好场所。据蒲先生讲,咏仁堂蒲家的先祖是北京人,八国联*攻陷京城后,随慈禧光绪逃难的车队到西安,后落户秦渡镇。到蒲先生这里,也算地地道道的秦渡镇人。蒲先生的先祖曾是清宫的酿酒师,爷爷辈在秦镇经营中药材生意。对酒曲的研究颇有见地,对*酒非常喜爱。平时自酿*酒,自食自用,乐此不疲。蒲先生自小受到爷爷的教诲,耳濡目染,掌握了 的酿酒技术,并利用家传的药酒配方,开发和研制出祛风湿酒、回春酒、补酒和消化酒。这些医疗保健酒销往西安、周至楼观等地,“咏仁堂”酒馆的名声日益响亮。
讲述秦镇的故事秦渡记忆89秦渡人与戏
发布时间:2020/7/23 17:17:35 点击数: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