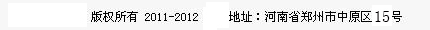中国西部散文学会
年第期总第期
桑枣熟成满眼诗又到桑树挂果时。桑树,在我老家是很常见的,与楝树、槐树、榆树、泡桐树一样普通,主要有两种,一种蚕桑,一种胡桑。蚕桑是由生产队组织人工栽植的,成亩连畴,郁郁苍苍的一大片,要的是它的叶,用于养蚕。蚕桑树个矮,枝条既长又多,叶片繁茂肥大,叶色绿中含*,水头足,很嫩。胡桑是野生的,散落在路边、田埂、房屋左右,树干瘦高,相对于蚕桑来说,叶小色重,呈深墨绿色,较老,常被采下喂猪。胡桑生长缓慢,一棵胳膊粗的树,往往要经过许多年,用胡桑树干做成的扁担,刚中含柔,富有韧性,可随挑担人的身形自然晃动,很好地消减肩头的压力,轻松而不伤身。在农村,有一根桑树扁担是很以为自豪,颇让人羡慕的。在人们的心目中,蚕桑只是类同于棉花的农作物,胡桑才是真正的桑树。孩子们吃的桑枣就是胡桑的果实。“门前不栽桑,屋后不植麻”是老家的一种习俗。桑与丧音同,开门见“丧”,自然不吉利;披麻戴孝是送别去世长辈时的规仪,屋后长麻,犹身后披麻,更是大忌。因而屋前肯定没有桑树,屋后不会见到苘麻的身影。当然,那屋指的是人居的堂屋,正屋。偏屋,厨屋不在禁忌之列。我家厨屋与猪圈夹巷中就有一棵胡桑,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的,根本没在意,直到树上挂满了果,才被我们盯上。树不算高,大约有我两人多高吧,也不粗,不及我的大腿,但结的果实好吃,比较甜,不像别处的那么酸涩。童年时代,桑树枣成熟时节,我的小罗罗朋友就特别多。我们天天盯着那一树果实,看着它们由青到红到紫黑。实际上根本不会等到完全成熟的紫黑,只要见到深红的就迫不及待地开吃,往往连刚泛红的也被一起狼吞虎咽了。在那贫困的岁月,干瘪的肚皮造就了我们超强的食欲,好吃的东西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桑树的果实,我们那里,既不叫桑椹,也不叫桑果,而叫桑树枣子。我知道这种果实叫桑椹时,已是离开家乡以后的事。把桑果叫成桑树枣子,仔细想想,是再贴切不过了。一个“枣”字,就将桑树果与楝树果、梧桐果、泡桐果以及其它树的果子区分开来,能吃不能吃,就这一字之差。再则,凡是枣,不管黑枣红枣蜜枣,在那时乡村人眼里,皆为营养丰富的大补之品,物稀价高,一般人消受不起。把桑果上升为枣,说明其不仅能吃、好吃,而且金贵。桑树枣子,叫着舒心,吃了开心,其中显然也隐含了对美好希望的一种寄托吧。 桑树似乎总是被不绝如缕的乡愁缠绕,承载的乡愁,超出其它任何一种树木花草,桑井、桑梓一直是故乡的另外称呼。乡愁不仅是对旧人旧物旧时光的怀恋,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一种思绪。乡愁不同于食欲,到时到点要进餐,而是似风似雾,来无影去无踪。乡愁是不经意的,就如家乡的胡桑树,它的种子不知是鸟衔来的、风吹来的,抑或是从那捆柴草中带来的,就那么悄不留神地从泥土里钻了出来,探头四顾,羞羞涩涩,静悄悄地生长,静悄悄地结果,无需施肥浇水,也不指望谁观赏、赞誉。乡愁的滋味基本就是桑树枣子的滋味,有点甜,有点酸,有点涩。“梦里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一个“桑”字,几乎可以浓缩像我一样、恢复高考后跳出农门、到城市讨生活的一群人的人生经历和心理历程:生于桑户、历经桑海、年值桑榆、心系桑梓;年轻时希望插翅飞离家乡,年老后希望时光倒流,回到故乡的童年。“情怀已酿深深紫,未品酸甜尽可知。”有桑树的地方就有家,那满缀枝头的桑树枣子,永远那么诱人,始终令人迷醉。岁月里的巴地虎“青箬笠,绿蓑衣”,诗里的笠就是斗笠,我的家乡叫斗篷。别处的斗笠多为竹篾编成,我家乡的斗篷则为苇篾编织。祖祖辈辈的故乡人,靠着这一顶斗篷,遮阳挡雨,劳作生息。往往,斗篷的主人离了世,那顶斗篷还在墙上挂着,像是一枚句号或是一声轻轻的叹息。
斗篷由篷顶、篷圈、篷带组成,圆椎形的篾顶是主体,篷圈、篷带是附件,起稳固作用。篷圈圆形、宽近一寸,类似电视剧中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我奶奶是编斗篷圈的能手,四乡八村闻名。她编圈速度快,别人编一只的功夫,她三花两绕可以绕出两个;质地好,精致密实,好用耐用;花式多,胡椒眼儿、菱形眼儿、方眼儿、圆眼儿,并间有鱼、鸟、花形于其中。编好的圈儿,一串串挂到墙上,*灿灿、红嘟嘟,惹人眼目,招人喜爱。
许多人便或远或近慕名寻到门上。人家给钱,奶奶一律不收。乡亲们淳朴,不好意思白要白拿,常常拎了一条瓜或几颗青菜来,一时间我家的瓜菜多得吃不了。也有揣个鸡蛋来的,奶奶都是给了篷圈而不肯留下蛋。那时鸡蛋金贵,一家一户的食盐火柴、针头线脑都指着这鸡蛋去换。从我奶奶手里撒出去的那些篷圈被缝制到篷顶里,构成了一顶顶实用的斗篷,云朵似的,飘逸在家乡的小路上和田野里。一茬一茬的庄稼种了、收了,一顶一顶的斗篷旧了、坏了,一个一个的人老了、走了,躺进了如同硕大斗篷的土墓中。 篷圈是用一种草的茎蔓编织的,叫巴地虎,也叫巴根藤。我家乡土地上盐碱疤随处可见,上面长不出庄稼,野草野菜也极少见,即使有,生得也很憋屈,稀疏、矮小。巴地虎偏偏在上面长得旺相,每棵三四根茎蔓,形似长长的铁丝,贴地而生,每隔一节,就会探出几根须爪,紧紧抓着地皮,节上顶着几枚瘦叶,那茎蔓通常长达一丈以上,有的可达两三丈,很结实,很有韧性。秋天用小锹铲下,晒成金*色或古铜色,就可以编篷圈了。 在白茫茫一片盐霜中,巴地虎 是一个生命奇迹,圆实的藤蔓一丝一丝向外拓展,细小的须爪不失时机地抓牢每一点可以抓住的土地,固定身姿,汲取养分,俨然刀尖上跳舞,步步惊心,稍一懈怠,就会叶落藤萎,化为尘埃。故乡人称它巴地虎,自然是敬佩它生命里具备老虎的那种力道和韧劲,生存过程中展示出的那种鲜明的虎形虎势。巴地虎顽强的生命力可与高山雪莲、戈壁红柳媲美,只要有一丝阳光、一滴水分、一星泥土,就会捧出一颗花朵、伸出一根枝干、牵出一条藤蔓,以自身的方式,挑战生存的极限,彰显生命的活力。巴地虎随着盐碱疤早在家乡绝了迹,斗篷也被草帽、太阳帽相继替代,没了踪影。然而,巴地虎的生命特质,已悄然植入故乡人的血脉;斗篷如花,粲然绽放在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岁月深处。野艾芬芳我的家乡,艾蒿叫做野艾,或直接简称艾,与白茅草、僵芦苇一样,田头、路旁、河塘边寻常可见。春雨一浇,夹杂在野草、野菜中间,齐嘟嘟地钻出土来。 清明前,浓浓春色中,野艾身枝初展,高不盈寸,碧绿翠嫩。我奶奶便掐那嫩芽回来,洗净,搅在玉米面里做饼,强调说明前艾吃了可以明目,要我们弟兄都吃。其实不必她说,我们都抢了吃。那饼带点淡淡的苦味,清香侵齿,滋味独特。每年吃上一两回艾饼,似乎成了我们家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奶奶去世后,这个规矩就随了她老人家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吃艾饼算是一种 了。那时粮食金贵,一家人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能吃稀的,绝不吃不硬的,能吃粗的,绝不选择精的。我奶奶一辈子省吃俭用,当年坚持做艾饼,莫不是寄托着老人家对她童年生活的怀念吧。艾蒿作为野菜,不同于荠菜、盐蒿、小蒜、枸杞头被大家普遍认可并接受。不过,吃艾也并非我奶奶的发明,古人食艾是有史可循的,而且吃法还不少。有如我家一样做艾饼的,有做艾糕的,还有将艾泡入酒中,制作成艾酒的,大约类似于现在的一些养生保健酒吧。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些并未普及并流传下来。乡村蚊虫多,对付蚊子一般都是燃烧蒲棒,那是菖蒲的果实,像点蚊香一样。要彻底灭杀或驱赶走屋内的蝇蚊蚁蛾、蟑螂跳蚤,除了农药,就靠野艾。用农药,对人畜有害,还费钱。用野艾,既无害又方便。关闭好门窗,拿几把晒干的野艾,在屋子中央的地上点燃,滚滚烟雾伴着浓浓艾香,从门窗的缝隙中钻出来,别人一见就知道这家熏蚊虫了。那香浓烈、自然、纯粹,有很重的泥土气息。端午节,家乡不仅吃粽子,还须割上一束野艾与菖蒲,插于屋檐下。人们把野艾看成辟邪之草,犹如神中的钟馗、树中的桃木,与病、与*、与邪、与魔势不两立,守护着人世间的安康。以艾禳病消灾,这种风俗流传已久,在国内还比较广泛。据古籍记载,端午前后,古人不仅遍插艾蒲,有的还把艾扎束成人形悬于门楣之上,并流行将艾做成虎形或将彩纸剪成虎形粘上艾叶,男子佩带腰间,女子戴在头上。试想,满眼都是腰挂艾虎的雄壮男子、头插艾虎的娉婷女子,那是怎样的熙熙攘攘、怎样抓人眼球的风景?病近不得身,邪靠不了边,乾坤朗朗,世界一片清明。秋日,野艾过膝,成灰白色,我奶奶便割了回家,做成枕胆,说枕了明目提神,我们那时枕的都是艾叶枕,松软、清香,觉睡得特别香甜。当然,乡村人更普遍的是把野艾作为柴禾,成熟的野艾,枝干有成人手指粗细,较玉米秸密实,与棉花秸、僵芦柴相仿,接近于狗骨树、枸杞杆,火猛、耐烧,比茅草、穰草受欢迎,烧出的饭,很香,锅巴更是又脆又香。偶翻《辞源》,见艾的辞意竟有八种解释,其中四解为:对老年人的敬称;美好;养育;报答。这更激发了我对于世事与人生的联想和对养育了我的故乡与已逝多年的奶奶的深切怀念。“风来蒿艾气如薰”,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够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野艾芳香。作者简介茅针,原名唐锦涛,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获得过省级以上报刊年度 作品奖和多种征文奖。本期责编:高彩梅
配图:网络
编审:*建明
投稿邮箱:bdr
.